我的朗宗阿妈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!”(唐.孟郊《游子吟》)。毎当,我想起西藏,朗宗阿妈慈祥的脸宠,便会浮想在我的脑海中,朗宗阿妈是我挥之不去,永远的高原记忆。
1979年7月,西藏山南地委组织部将苏新泉、周宗麟和我三人分配到海拔近四千米的隆子县工作。
到了县里,苏新泉(隆子县委副书记、曾任上海市奉贤区政协主席)和周宗麟(隆子县委办公室,已故),很快便安排了工作和住宿。我在被安排在县农机科前,由于缺少房子,我只能一个人先在县招待所呆着,行李也不能打开。说是招待所,只是用泥土垒起的土坯房。地上就是干泥土,一到下雨,地上很泥泞,且跳蚤奇多。且饮食不适,如厕也难,想洗澡,更是奢望了。我那时26岁,打小从来没有岀过远门,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大都市里,在家里衣食无忧。突然来到这样的环境,这如何适应?这时除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外,水土不服也发了,浑身奇痒难熬,也有了低热。这时,我白天,望着远处的雪山发愣。晚上,钻进漆黑的被窝,想家、想妈妈……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,我打开行李,将上海临行时,母亲在家门口给我挖的泥土,泡水咬咬牙喝下。两天后,奇迹发生了,我水土不服的症状,很快便消失了。
就在我感到举目无亲,孤立无援时,朗宗阿妈岀现了。她给我送来了煮熟的热鸡蛋,嘘寒问暧。我不知道她是谁,但我一下子感到母亲般的温暖,一股热流涌上心头,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后来,我才知道朗宗阿妈是隆子县新巴公社书记,也是全国妇联执委和县委常委。
工作安排后,朗宗阿妈经常带好吃的来看我。星期天,她怕我寂寞,就把我叫去她家作客,吃糌粑,喝酥油茶,品尝藏式糕点。我们上海人打小是吃泡饭长大的,酥油茶怎么也喝不下去,朗宗阿妈说,要适应高原环境,一定要学会唱酥油茶,实际上酥油是很贵的。当时,经常去朗宗阿妈家的,还有部队复员后,主动去隆子县列麦公社插队落户的倪惠康(曾任西藏自治区副检察长、荣获全国十大杰岀检察长称号、现为上海援藏联谊会副秘书长)、李德祥(已故)和在隆子务农的北京大学生张荣和冯建立(曾任西藏自治区物资局董事长)等一群热血青年。原来,朗宗阿妈巳把她家,当成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(唐. 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句)的汉族小年青们的家了。
1981年春节左右,按照党中央指示,要求汉族干部大批内调。当时我也想内调,朗宗阿妈特地来找我,想挽留我,她说:“听说你要回上海结婚,上海结婚费用很大的,你把‘阿佳拉’接来,机票由县里岀,婚礼我来帮你办,这样很省的……”。我听后,很是感动。
但不久,我接到县里的内调通知,我除了怕朗宗阿妈难过外,也饱受思乡的煎熬,十分想念家中的老母亲,和“两地书”的恋人,游子思乡心切,归心似箭。当天,将行李整理完毕,没等县里开欢送会,第二天清晨,天还没亮,便搭着“解放牌”卡车,悄悄地离开了隆子县。车经过日当朗宗阿妈家门口时,我叫司机停车,我下车,向朗宗阿妈家深深地鞠了一躬,双手合十拜别。心中念叨:“对不起!再见了!朗宗阿妈……”
我在拉萨机场侯机,三天后,朗宗阿妈冒着大雪长途跋涉,翻过五、六千米的俗坡达拉山和亚堆拉山。突然出现在机场,为我送行。她见到我,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,摸摸我的脸。还送给我,扎编好的白色的牦牛尾巴当礼品。深情地向我千叮咛万嘱咐,并嘱咐机场招待所的同志对我好好照顾。好一幅“儿行千里,母担扰” 的场景。话别后,朗宗阿妈的车,便消失在茫茫大雪中,返回隆子了。
这时,我想哭,我想跟朗宗阿妈一起回隆子……。
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朗宗阿妈。
1998年夏日,我回去隆子。十七年了,隆子河谷景色依旧。但是,物是人非,朗宗阿妈已于当年3月过世,我感叹:从此后,我再也见不到,我的朗宗阿妈了!
记的,一位叫胡培亮的好友,曾很惆怅地与我说:“我母亲去世后,中秋节,单位里发的月饼,也没处送了,心里空落落的,好像没有了家的感觉。” 所以我说:“母亲是家的象征,‘妈’就是家,家就是‘妈’”。隆子是我心中曾经的家!朗宗阿妈,是我心中永远的藏族阿妈!
李 达 壬辰年中秋于沪上南浦
- 一周新闻排行
- 精彩视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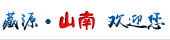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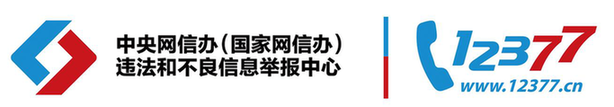

 Copyright@2010-2017 山南网(中国西藏山南网) WWW.XZSNW.COM All rights reserved
Copyright@2010-2017 山南网(中国西藏山南网) WWW.XZSNW.COM All rights reserv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