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冻土“对话”36年的青藏铁路建设者
2006-05-09 00:00:00 来源: 新华社 作者: 文贻炜、侯德强
张鲁新是青藏铁路线上坚守时间最长的建设者,59年人生中,雪域守望36个春秋,只为解决“冻土”这一建设高原铁路世界性难题。
情定雪域
平均海拔4000米,位于“生命禁区”,建设世界海拔最高、难度最大的高原铁路,张鲁新的命运与冻土紧密相联。
建设青藏铁路必须确保冻土的热稳定性。世界上在冻土区修筑铁路已有百年历史,但效果不十分理想。据俄罗斯1994年调查,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,线路病害率达27%。运营近百年历史的第一条西伯利亚铁路,1996年调查的线路病害率达45%。
为建设青藏铁路,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,铁道部就在青藏高原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,建立了冻土科研基地——风火山观测站。
1970年,张鲁新从唐山铁道学院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,投身铁路建设事业,开始涉足多年冻土地区的工程技术工作。
为确定冻土性质进行地质化验,张鲁新与一同伴一年曾挖437个试坑。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,呼吸正常人一半的氧气,一个试坑挖下来,累得气喘吁吁。
他们没雇临时工,就是招来临时工也吃不了那份苦。进行有关冻土的全方位调查,他们每天单调地重复着:一天走十几里路,挖坑、试验、填图。
为确定青藏铁路路线方案,1975年,张鲁新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程国栋等7人去错那湖一带考察。
开始,他们坐解放牌卡车,卡车陷进去了,他们就骑马,马陷进去了,他们就步行。在雪域高原考察,往往几天不见人烟,只有地上的野驴和天上的苍鹰与他们作伴。
在寂寞难耐的环境中,他们在冻土区南界坚持了8个月。虽然享受政府特批,但每月供应他们的,仅是一斤白糖,一包茶叶,几瓶军用罐头。
与死神擦肩
进行高原冻土研究,茫茫雪域,孤独与危险时时相伴。
1976年7月,张鲁新一行三人到尺曲河一带考察。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,搅得天昏地暗,他们迷失了方向。
暴风雪停止了,乌云没有散去。他们意识到越走越远,越走越危险,最后只好坐在一个山坳里等待同志们来解救。白天与黑夜交替了两个轮回……
张鲁新平时喜欢吃糖,衣袋里放着的3块糖,是他们3人的唯一食粮。
大本营里,程国栋等人苦苦等了二天不见张鲁新归来,预感出事了,急忙带人出去寻找。
为了找到张鲁新,程国栋决定兵分三路,打着火把,顶着夜色,在空旷的荒原里他们含着眼泪高喊着张鲁新等人的名字。
黑夜里,张鲁新3人已经筋疲力尽,他们听到了远处同事的呼喊声,却无力回应。
“怎么办?我们等死吗?”
“火柴盒里还有三根火柴,用火柴给同志们发个信号。”
没有料到,第一根火柴划着后即被风吹灭了,同伴要划第二根,被张鲁新制止了。
张鲁新说:“你不是还有一个纸烟盒吗?把纸烟盒撕成3个纸条,用火柴点燃纸条,一条接一条地燃下去,同志们或许会发现我们。”
同伴照此而行。沉沉黑夜中的那一丝亮光,被程国栋发现了……
记不得多少次与死神擦肩。科学考察中,张鲁新遭过土匪抢劫,因身上没有财物,躲过一难;他曾因食物中毒,吐了两天两夜,在高原上硬挺着活了下来;一次途经唐古拉山,大雪封山半尺多厚,司机不敢开车前进,张鲁新下车,在前面趟路引导司机开车,风雪中跋涉30公里,最终冲出死神魔掌……
上世纪80年代,由于工程技术与国家财力等问题,青藏铁路建设在格尔木划上“暂停”符。
从事青藏铁路冻土研究的100多位专家,相继调走、改行、退休。张鲁新与少数人留了下来,怀着坚定的信念继续守望雪域。
家人无私的爱
2001年6月29日,青藏铁路建设正式开工,张鲁新被聘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,成为筑路大军“军师”的他,以工地与总指为家,与妻子见面的日子更少了。
离别相思,在妻子李郁芬的生活里,早已习以为常。1974年冬,他们婚后才一个星期,张鲁新便上了高原。此一别整整3年。
1977年,李郁芬调到兰州市邮政局当了一名信件分拣工。她到兰州时,张鲁新还在风火山工地,是他的朋友到车站举着写有李郁芬的牌子将她接回。
对此,李郁芬没有怨言。既然嫁给了张鲁新,理所当然地把爱献给高原。
1978年底,他们有了儿子张楠。儿子刚满月,张鲁新就上了唐古拉山。1980年春节他下山时,孩子都会跑了,儿子见到陌生的他直喊“叔叔”,硬是不让他进家门。
就是这样,妻子也没埋怨过丈夫。她知道,在冻土研究和家庭之间,丈夫倾向于前者。
为此,张鲁新曾被邻居批评:“老张,你好狠心呀,你一年四季不在家,李郁芬冒雨去买粮,一手打着伞,一手提着粮,打伞的臂弯里还要坐着你的儿子,负重爬6层楼,你心疼不心疼?”为此,他难过地哭了一场,但几天后,他又上了高原。
张鲁新母亲是一位知识分子。1975年1月,父亲给他来信说,母亲患直肠癌到了晚期,希望他回去和母亲见上一面。
张鲁新从西藏赶回山东,刚刚坐在母亲的病床前,母亲就说:“新儿,你为何不把外语书带来?研究冻土,不以苏联的冻土作参考你还研究什么冻土?研究苏联冻土,不学习俄语,你怎么去研究?”
这样,回家的半个月,照顾母亲和学习俄语成为张鲁新的双重任务。母亲看到儿子很努力,十分欣慰:“待我死的时候,你不要回来了,好男儿志在四方,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说,事业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”
1975年11月,母亲去世,那时张鲁新正在西藏那曲的大草原。母亲弥留之际,留给张鲁新的话是:“新儿,西藏是个很好的地方,你要在那里安心工作。”没能与母亲诀别,是张鲁新心中永远的伤痛。
家人无私的爱,赋予张鲁新事业追求强大的动力。办公室内,一叠叠来自国际、国内的证书与荣誉,证实张鲁新36年雪域高原坚守的成就,让他实现个人对国家的最大价值。
想家时,只能轻抚相册,或电话传音。但张鲁新是幸运的,建设青藏铁路成功破解“冻土”这一世界性难题,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与梦想,他能亲历与见证。
儿子张楠今年28岁,他并不了解父亲张鲁新。在他的人生中,父亲和他生活时间的总和不到两年,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。
大学毕业后,张楠赴俄罗斯留学,取得硕士学位,而后赴英国留学,并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。不久前,张楠走上青藏高原,他说,我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爸爸……
文章来源: 新华社
作者: 文贻炜、侯德强
- 一周新闻排行
- 精彩视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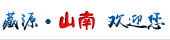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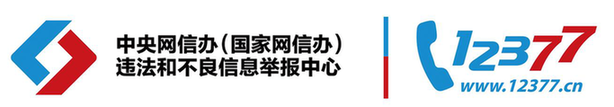

 Copyright@2010-2017 山南网(中国西藏山南网) WWW.XZSNW.COM All rights reserved
Copyright@2010-2017 山南网(中国西藏山南网) WWW.XZSNW.COM All rights reserved